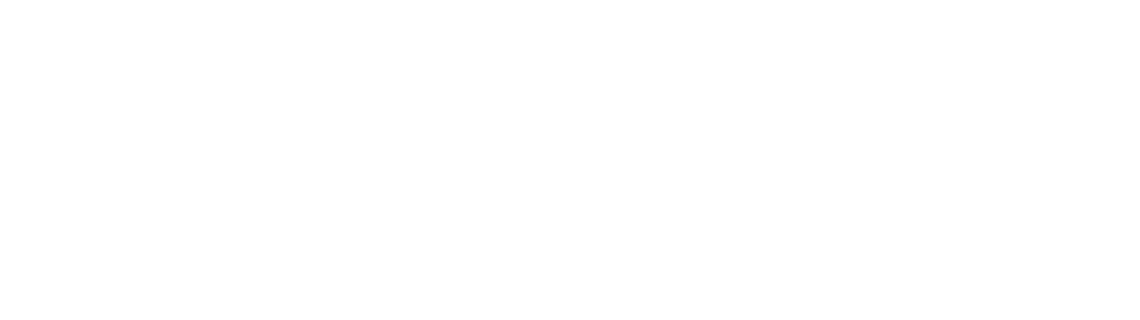佛经出版-正规出版 自费佛经出版
太平天国的排除异己宗旨,使传统文化受到重大摧残的,不仅儒家经典和儒家著作,佛教寺庙和经疏在太平天国地区也遭到同样境遇。佛教不是我国的本生宗教,但自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我国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由于读书人的参与,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遂产生天台宗、华严、唯识、禅宗、净宗、密宗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宗派,这些宗派的综合,构成中国佛教,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思想对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思想、伦理、风俗,甚至语言都有深刻影响,所以研究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不可离开中国佛学;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如果您知道一些佛学,会理解得更深刻些。北京经书出版
人们往往将佛教和迷信等同,其实,佛学和迷信是两件事。佛教所以在我国能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青睐而研究,在于原始佛教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波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人人平等、博爱、和平相处的佛教,流传于我国的是大乘教派,大乘派的宗旨,概言之,强调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自利利他并重。大乘佛教的多神教原则和平等思想,与我国当时政治上的强调血统的寡头豪门统治形成反差,所以能获得一般读书人的共鸣;而自利利他,以及舍身饲虎等佛本生故事,又和我国儒家待人以仁,处事以义的原则相一致,和汉族的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传统相符,所以能获得读书人的接受。我国儒家经典,或说早期的儒家学说,原来仅仅是使国君施仁政的规范,所以基本上不涉世界观,《书经》中有些“天命”、“革命”等,仅是一些粗敝的欺人之谈。春秋诸子涉及一些世界观,但他们关心的仍是政治。魏晋时,由于长期社会动荡和门阀制度,产生玄学。佛教经论就具有较深刻的,解释宇宙事物,这显然吸引我国读书人的注意。如魏晋时进入我国的般若学,发展成为注重于教义研究,所谓“般若派”,是当时重要教派。他们信从“般若部类”的《大般若经》,就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而得名。这组经讲把整个宇宙分成“色”、“心”两部分。“色”在一定意义上指物质世界,“心”指精神世界。并认为两者都是假名,没有实体,故说性心是空,别名“空宗”。这种学说和当时流行的玄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能被人接受、研究,并与我国传统思想结合。玄奘所译《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亦可见这种思想影响之深。北京佛经出版
中国汉地佛教,佛学到中唐极盛,并形成8个派系: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相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足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叉名真言宗。习惯简称性、相、台、贤、禅、净、律、密。9世纪后期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后,寺院、经书、佛像毁坏殆尽,但已融入我们思想的佛教思想是无法剥离的。所以一经政治变化,10世纪天台宗的经典就从朝鲜流回,不久贤相宗的典藉又算复兴,其他宗派典籍亦陆续有所恢复,但法性守,法相宗始终没有找到典籍而无法恢复。虽然中国佛教从宋代后有所恢复,但终没有中唐时期那么盛,可是学者对佛典的研究代有成就。到10世纪70年代宋代朝廷开始刻大藏。此后元明清官家、庙宇均有大藏刊刻。经书出版
如果说太平天国开始时,洪秀全还对儒家经典进行修改,表示其中还有他能接受的部分,那么对佛教,他是丝毫不能容忍。太平军所到之处,寺院、经典均一扫而空。我国民间明末、清初所刻的《嘉兴减》的版片全都烧光。佛教虽然代有大藏经刊刻,由于篇幅巨大,亦仅仅收藏在名寺古刹,民间所有都是常用经典。太平天国后,全国仅存北京柏林寺所藏清代政府所刻“龙藏”,刷印龙藏是要和皇上商量的,所以读书人无法获得研究用的佛经。经书书号
在共同的活动地域上,人们还必须有共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和相近的习俗,还有经济,这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丢掉了,就不再是原来的民族,只是一堆人而已。民族经受灾难,如果文化受到打击、侵蚀,首要的就是恢复文化。恢复过程中自然也包含吸收新的文化。我国的近代,大致就是这过程。
历来佛典的刊刻是中央政府和寺院。太平天国后,地方官书局他们虽为恢复文化而出书,但汉地佛典他们不方便插手。而寺院,因为地方刚平静,经济正逐步恢复,信徒不可能有很多施舍,刻经更有困难。任何人群和事物都是分层次的,接触佛教的人也是有层次的。绝大多数接触佛教的是善男信女,他们对佛极虔诚,很多是迷信,多数并不研究佛学,佛典的缺乏就不显得严重。然后就文化的延缓、发展讲,当代重要的哲学史家任继愈讲:“儒家学说当然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然而它并不是我国文化传统的全部,自隋唐以来,佛教经典逐渐被我国知识分子吸收,成为我国传统的不可分的部分。”缺少佛典就是种缺陷。前面提到,儒家原始学说着重在政治,他们的伦理着重在社会秩序,就社会伦理文化的全面需要讲,略有欠缺。就被历代儒家赞之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而言,其中相当多采自佛教。《四库总目》说:该书在“《唐志》、《宋志》俱列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可见我们的社会思想不能抛开佛学来研究。佛经出版
这时在江苏有几位从事佛典的出版,有禅师,有居士。最早从事的是杨文会所办的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字仁山(1837—1911)生于安徽石埭(现太平)诗书之家,家中略有田产。父亲中进士后任刑部主事。文会自幼性好读书,即在战乱仍不间断,广泛阅读儒家经典,诸子百家,音韵天算,舆地史学大都通晓。他性情豪迈任侠,太平军进入安徽后,在社会和家庭影响下曾办过团练。后来在张芾,周天爵幕,曾国藩进南京后,入曾国藩幕,办理谷米局。曾国藩幕中学者众多,精于佛学的饱学之士不少。同治三年(1864)杨在乡养病时接触《大乘起信论》,引起他对佛学兴趣,现在有那么多朋友,正是潜心钻研的好机会。兴趣与钻研是相互推动的,随着研究兴趣的增高,就觉察到没有佛典的严重性,加以金陵书局刻书已有成绩,有所借鉴,所以立志刻经。
杨文会借鉴金陵书局成规,与同好商量,订立章程,于同治五年(1866)成立金陵刻经处。当年就刻了《净土四经》。此后杨文会一心从事刻经事业,婉谢了曾国藩、李鸿章几次保荐,而以传播佛经,有助于祖国文化发展为已任。
如果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经律,仅仅能提供一些广大信徒的信仰需要,仅仅是普通宗教,而不是为了供应研究者的需要,研究者需要更多特定的经,不同宗派的经典彼此有所差别,所以佛教的经、律、论总数很大。佛教典藉在公元2至11世纪翻译成汉文的经、律、论共有1690余部6420余卷。10世纪宋政府开宝年在四川刻的《开宝藏》仅5048卷,缺少的400卷就是会昌灭佛被毁后未能找到的。11世纪福州民间第一次集资刻《崇宁万寿大藏》,有6434卷,其中有新译的。大藏经宋代前后有6刻,元、清也都有刊刻,明代在南京时刻有大藏,称南藏;朱棣攻南京时经版毁于兵灾,迁都后在北京重刻,称北藏。因为北藏属于宫中,请经手续麻烦,所以五台山的僧侣发愿刊刻,以广流传。从明万历十年(1582)到清康熙十六年(1677)近百年才刻成。开始在山西五台山,4年后移到浙江径山寺兴圣万寿禅寺、寂照庵等刊刻,后来经版移到椤严寺,供人刷印。这部大藏经因而有3个名称:《嘉兴藏》、《径山藏》、《楞严藏》。《嘉兴藏》正藏计6300卷。它有两个改进:一是改宋代刻经仿照“贝叶经”的样子形成的经折装传统为“方册”,即线装本。“经折装”印好后要裱几层纸,再折成折子。这样一部经用的纸张和装工都很费钱。而线装只要单层纸对折用线一钉就成,费用低,便于普及。第二是将“经”和“疏”合刻在一起,方便学习者。儒家经典因为成书年代久远,名物意义和词义变化,所以经书历来有注疏,进行解释,学习者根据注疏学习,才能较为方便和正常理解。同样,佛经来自印度等地,翻译时间大多在公元二至十世纪,已有千余年时间,不仅词汇意义有所变化,而且当年佛经翻译已有较多外来语,所以后来陆续有所注疏。历代刻大藏经,为了所谓尊重经,疏都另外单刻。虽然似乎尊重了经,但有人并不知道某经有疏,对研究者很不方便。《嘉兴藏》则将有疏诸经与疏合刻。所以诸大藏中《嘉兴藏》最好。因为《嘉兴藏》经版已经被毁,杨文会计划重刻《嘉兴藏》。
刻一部大藏,实属大工程。历来民间刻藏都作为功德,由寺院主持其事,依靠众多信徒捐献。金陵刻经处则很难广泛募集捐献,而大藏中绝大多数经仅仅少数学者需要,不能靠以经养经的办法,所以杨文会决定缩小范围,选刻一半,称《大藏辑要》,他与同志编就的《辑要》目录共收经疏460部,3320卷。其中特别有会昌灭佛后中土始终未能找到的法性宗、瑜伽宗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法性、瑜伽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法性宗、瑜伽宗诸宗中土原已失逸的佛经,是杨文会托在伦敦认识的日本佛学人士南条文雄在门本陆续寻觅到的。有此三者,所以《大藏辑要》虽然仅及《嘉兴藏》一半,但其价值很高。金陵刻经处不仅仅刻经,同时还在处所创办祗洹精舍作讲学的场所。他自己讲授过《大乘起信论》;晚清的诸多名人:如谭嗣同、章太炎、欧阳竟无、汪康年、夏曾佑等人,都曾在那儿听过佛学,在他们的著作中,如谭嗣同遗诗中有《金陵听说法》三章,在《仁学》中也有反映。欧阳竟无还进而创办支那内学院,成为南方研究佛学的场所。
综观历史和现实,佛教以博爱为宗旨,对待不同信仰的人也以平和、友爱相待;佛教徒和居士值得称颂的是,历来刻经没有门户之见。如妙空,他崇尚净土宗,他刻“空经”全经《大般若经》,刻至第425卷时染重病,自知难免,希望清梵法师刻完其余175卷。杨文会请南条文雄找到和刊刻中土久逸的性、相诸宗经典,也都是毫无门户之见的事。我们必须将迷信与佛教区分开。赵朴初说:“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和国外的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兴旺情况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亟待进行。如何恢复我国佛学以与祖国当前的伟大时代相适应,还需要佛学界有识之士发大愿心,继承先德未竟之业,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172页,上海辞书,插图本,1999)